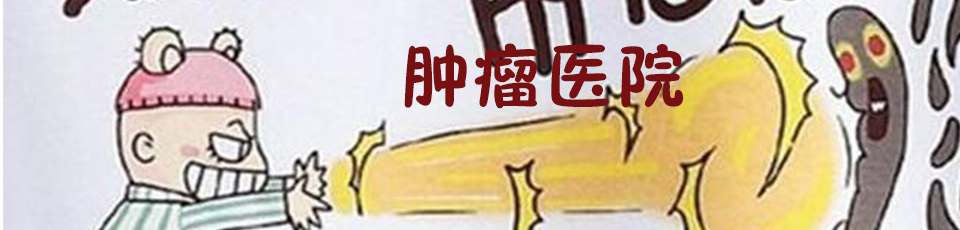牛痘,怎样理解才是一个类比推理的案例
类比不仅是人们推理论辩的工具,它也同归纳一样,是人类的知识之源(尽管有时不太靠谱。)
三十年前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逻辑学课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普通逻辑》,书中许多引述了大量自然科学史中的案例,比如,在讲到类比推理的时候就写道:
“英国医生詹纳发现‘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这是受挤奶女工感染了牛痘而不患天花的启发。”
就这么短一句话,它该怎么理解为一个类比推理的案例呢?原书语焉不详,学生只可意会。
多年以后,我作为一个评论课教员,在讲到类比推理时候不免就想到、用到了这个案例。
但我的理解是错误的——直到我昨天读到本月出版的今年第31期《凤凰周刊》封面文章《天花消灭30年后:传染病抗争史》。
那么,我一直是怎么理解《普通逻辑》中关于牛痘那个案例中的类比推理的呢?
我是这么想的:牛在感染了天花病毒之后没有死去,因此获得了免疫力;而挤奶女工因接触牛而感染了轻微的天花病毒,也就在不觉间获得了免疫力。而詹纳医生则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牛与人在免疫这个生理层面上的类比关系。
所谓牛痘——也就是从牛身上提取,后注射进人体,不会使人死亡却可增强免疫力的病毒,不过就是“疫苗”这个抽象概念所涵盖的万千品种的一种而已。
这样,我实际上从当年《普通逻辑》课本中那句简短的话出发,下意识地假定了詹纳医生是从牛和挤奶女工身上直接发现了疫苗的原理。即:为人注射传染病疫苗的原理是从挤奶女工通过牛感染了天花病毒而对天花免疫中获得的直接启示。
但在阅读《凤凰周刊》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的理解是错的。
在这组封面中的一篇——记者段宇宏写的《与天花的斗争,人类第一次完胜了死神》中写道:
……天花历史悠久的中东和印度,很多医生观察到一个现象,一个人如果早年患上天花并幸存下来,此后不会再被传染。
从观察到的现象中得到灵感,有人提出自然感染法,即刻意从轻微天花患者身上取脓液感染自己,以此获得免疫力。但自然感染法的风险极高,很多人因此丧命。年,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给国内朋友写去一封信,告诉他们当地流传一种天花预防技术,不是由医生而是由农妇来操作:从病情轻微的天花患者身上取少许脓液扎入健康者皮肤之下,让其接受感染,经过轻微症状后如果没有死亡,那么将对天花具备终生免疫力或部分免疫力。
————
由此可见,具有天花免疫力的“人痘”接种,其实要早于牛痘。
由于蒙塔古夫人的勇敢实践和大力宣传,“人痘”接种被引入英国,到年完成20万例接种。
只是因为接种“人痘”比牛痘的死亡率和失败率高得多,才有了后来詹纳医生对牛痘的伟大发现。也由牛痘的发现,人类才最获得了以“疫苗”应对所有传染病的基本原理。
詹纳医生也正是在农民接种人痘的过程中才发现了牛痘效应的:
他发现一些人接种人痘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应,“经过询问得知这些人都是奶场工人,从牛乳头那里染上过牛痘。詹纳早就听过民间传闻,说挤奶工对天花有免疫力,他一直认为这只是迷信,现在他开始重视这一传闻”,并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做了成功的实验:
他从一个挤牛奶女孩手中的牛痘脓疱中取出痘苗,接种到一个男孩的手臂上。男孩七天后感到手臂略有不适,第九天有点头疼,没有胃口,第十一天一切恢复正常,手臂接种处流出一点脓液,跟天花出液症状相同。两个月后,詹纳再次给这个男孩做人痘接种,结果男孩再没产生任何症状,对天花有了完全免疫力。
[报道配图:19世纪,法国学校内,新兵正在接种牛痘。请注意,在画面中央的案子上,好像真的躺着一头被捆住四肢的牛哎!]
从詹纳医生年做的这个实验,到年世卫组织宣告人类完全战胜天花,其间余年是牛痘这种科学有效的天花疫苗不断传播和优化的过程。这看起来时间较长,但比起天花肆虐人类的数千年历史,则要短得多了。
“詹纳被后世尊为‘疫苗之父’当之无愧”。
——我想,这个评价并不是因为他首先发现了疫苗免疫这一克服传染病的原理,而是因为他在前人对偶然个案的观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具有专业精神的科学实验,这才使他获得了与失败率和死亡率较大的人痘相比完全无风险,因此真正可以称之为疫苗的东西——尽管那个东西最初只是牛痘。
我们应当在英国工业革命的科学背景中理解这样的实验精神,应当从达尔文环球航行,在对万千物种的观察中发现生物进化原理的意义上理解这样的实验精神;应当从牛顿从“被一只苹果砸中了脑袋”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从瓦特受“沸水顶开壶盖”的启发发明蒸汽机的意义上理解这样的实验意义。
应当在科学实验的意义上理解类比推理作为人类知识来源的意义及其限度。类比只是开启了一个认识空间,指出了一个认识方向。
而相较于近代科学具有专业性、规范性的实验精神和实验过程,最初启发科学家认识灵感的类比思维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它的作用也许被逻辑学教科书夸大了——就像苹果砸中了脑袋、水蒸汽顶开了壶盖,对于发现万有引力、发明蒸汽机并没有那么重要一样。
回过头来说,牛痘作为类比案例的作用,体现在牛痘与“人痘”的类比关系中,也许应该这样理解:既然从天花的微轻患病的人身上提取脓液(人痘)可以使其他人获得相应的免疫力,那么从天花的微轻患病的牛身上提取相应物质(牛痘),也可能使人类获得相应的免疫力。
其间更具体的物质关系和物质过程,用下来的话表述可能更准确:
“牛痘病毒与引起人类天花病的天花病毒具有相同抗原性质,人接种牛痘疫苗之后,也可以同时获得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
这样看来,普遍存在的,是一种可以使不同物种产生免疫力的抗原——即“能够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并能与免疫应答产物抗体和致敏淋巴细胞在体内外结合,发生免疫效应(特异性反应)的物质”。
这是我们大千世界普遍联系的一个证据。而世界的普遍联系,则是类比这种思维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普遍有效的物质基础。
免疫力的原理并不是在这种类比中发现的。在这种类比中发现的,是一种具有免疫力的抗原从牛到人——跨越物种仍然有效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跨越,使人类不再局仅于最初的个别经验,而获得了对“疫苗”的普遍性认识。
而牛痘的实践价值则无非是这一条路径可以比原来的另一条路径——人痘——更为安全。
如果我们不了解科学史中关于接种“人痘”这一段过程的知识,就不能准确地理解牛痘作为类比案例的机理。
如果脱离科学史的完整背景,脱离更早、更多的人们积累的观察、实践和经验,被选入逻辑学教科书的孤立的科学案例,就像是神话一样。
逻辑学作为“思维的科学”,是人类的思想实践(包含试错)的结晶。而科学探索正是最活跃、最典型的人类思想实践本身。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掀起过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的命题中,“思想”与“实践”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而我之所以使用“思想实践”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在评论课上讲解逻辑学的来源的时候一直觉得:指导人类实践,往往通达实践的思想活动本身,也具有实践的意义。一些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思维方式被人们保留、提炼为逻辑推理方法(其中承认结论不完全为真);而被实践证明无效的思维方式,则在逻辑学中划归为“谬误”。
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史案例作为普通逻辑案例的价值的。而牛痘的科学史则使我认识到:也应当按照科学探索的真实过程正确理解这样的案例。
此外,我以往在课堂上讲到类比推理,提及牛痘时,还有一个错误:我以为人类到现一直在接种牛痘呢。我甚至在课堂上还问同学们的胳膊上有没有小时候注射牛痘的疤痕。
但阅读《凤凰周刊》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最终宣布:人类已经彻底消灭天花。而中国则自年起逐步取消了牛痘接种。
这样,坐在课堂上的90后同学们自然没有接种过牛痘,恐怕他们连听也没听过说。
[当年的宣传画《阿姨替我们种牛痘》已成收藏品,价格竟达数百元。]
这样看来,以牛痘作为类比推理的案例,可能真是太老、太旧了。
但在天花被牛痘消灭30年后,人类仍然在与许多历史悠久的传染病抗争着,目前仍然看不到止境。鼠疫这个可能被人们认为早已灭绝了的古老的传染病,最近就小小地惊扰了住在北京的人们,而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
也许,这正是《凤凰周刊》发表这一组封面文章的背景,也是新闻周刊这一类喜爱历史主题的媒体在网络时代的价值。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ningbohuodai.com/yyfg/7976.html